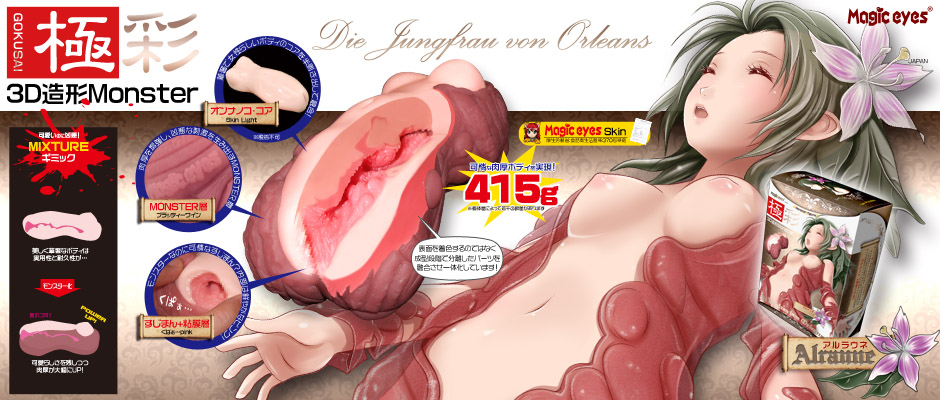我的小姨子剛結婚丈夫就去世了,因此長期住在我家,由於工作關係,經常白天在家。一次我出差回來沒有上班就在家上網,我以為家裡沒人就在瀏覽成人網站。
“好哇!你在看黃色網站!”突然我的小姨子闖了進來,原來她在午睡,起來上廁所。
“你…我…”我一時無語,看見我的小姨子穿了一件肉色絲質吊帶睡裙,且沒有穿胸罩,兩顆乳頭清晰可見,早已蠢蠢欲動的小弟騰地勃起“我沒有…”
“還說沒有?你看你…醜不醜?”她竟然指了指我的小弟。
我早就垂涎于她的美色和惹火身材了,我一把將她拉入懷裡“小丫頭,不害羞,看我怎麼教訓你!”摸著絲質吊帶睡裙,更加激起了我的慾望,我堅硬的弟弟頂著她肥大圓潤的屁股,一只胳膊緊緊地按壓著她碩大而富有彈性的乳房。
“我怎麼不害羞啦?”她在我懷裡象徵地掙扎著。屁股說不清楚是掙扎著離開我的小弟弟還是用力頂了頂。
“你看你,內衣也不穿…。勾引姐夫我?”
“瞎說!我怎麼沒穿?”我知道她沒穿胸罩,但穿了丁字褲,但我故意撫摩著她她肥大圓潤的屁股說:“哪裡穿了呀?,怎麼摸不到呀?…”我在她耳邊似吻非吻地呵氣,弄的我的小姨子已經方寸大亂。我將她推倒到床上說:“我看看你究竟穿了沒有?”
當我撩開她的睡衣時,果然是件T字性感內褲,看得我雙眼發直。白色透明的細細的一條內褲緊陷在雪白股溝中,形成美麗的景象,窄布遮不住整個陰戶,左邊陰唇露出一些,兩旁盡是包掩不住的陰毛,宣示著主人的性感,我的小姨子臀部高聳地趴在床上,極具挑逗的褻衣,使我不能自持,我趴在我的小姨子背上,用堅硬的弟弟頂著褻衣包裹的肥碩的陰戶,一只手從揉捏著絲絨一般光滑細軟的肌膚,一只手從下面握住了她高聳的雙乳。她尖叫一聲,並用陰戶在我的弟弟上摩擦,“不要…不要…姐夫…”她嬌滴滴地聲音反而促使我更加大力的揉捏撫弄。
我用掌心托在她乳房的下方,十指向上扣住乳峰尖端,左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正好夾住她逐漸堅挺的乳頭。一會兒按下去,一會兒抓住扯起來,一會兒左右抖動,一會兒揉面團一樣揉搓。
最後更是用指間夾住她的乳頭,微微挑搓起來。我的小姨子面色也越來越紅,而且身子也不再扭擺得這麼厲害,只是被我刺激得一跳一跳的。她的口中不再叫喚,轉而吐露出嚶嚀的細細嬌喘,身子軟化下來。
“姐夫…我…癢…受不了…”她隨著我的搓弄,渾身酥軟下來。
“哪裡癢…我的小姨子?”我將手移到她的下體,想脫下了的蕾絲內褲“不要!”
她輕聲抗議。伸出一只手去保護她豐滿肥碩的陰戶,突然一把抓住我火燒般勃起的巨大肉棒,“好大、好硬啊!”她居然把我的狼牙棒捏了一下,我順勢握住她白嫩小巧的手,不讓她脫離我的弟弟,她乖巧地套弄起來,把我的狼牙棒搞得更為膨脹,簡直就像要脹裂開來一樣。
我則將她的裙子挽到其腰間,露出雪白粉嫩股腿,小心將狼牙棒尖端對準她柔軟的花園密部。
“不要!”她搖晃著腦袋。
我緩慢而堅定地將狼牙棒向上頂去。
“嗯,你┅┅你┅┅”她雖然渾身酥軟無力,此刻仍然拼命向上躲避。
我巨大的龜頭隔著薄薄的蕾絲內褲,擠開她細細的蜜穴唇瓣,開始颳擦著她多汁的甬道肉壁,逐漸深入。她完全無力了,失去了躲避的能力,那種肉棒填塞的刺激讓她酥麻顫抖。她渾身哆嗦,連著蜜穴內部都哆嗦起來。逐漸將她的內部控製住。
“嘻嘻,你看,內褲都弄濕了呢。”
“沒有。”她隨著我的搓弄,喘息著、下體顫抖著。我伸手將她的陰蒂扣在手指間,揉捏起來。
“啊!不要┅┅”劇烈的刺激讓她渾身都震顫起來。“姐夫,你不要弄┅┅啊!啊┅我受不了的┅啊┅啊!”
我的小姨子渾身都在發顫,情難自禁的扭動嬌軀,淫水一股一股的蔓延流淌。
她猛地啜泣起來,身子軟軟癱倒在床上,一動也不敢動。我將她翻過來,“不…
…不要……嗯……啊……不要……“她的聲音愈來愈細,可是,我卻吻住她她的嘴唇。她緊閉著雙唇抗拒,我則不斷的用舌頭企圖把它頂開,隨著我手指的撚動,她下面的淫水已經汩汩的流了出來,雙唇也放鬆,我順勢將舌頭伸進她嘴裡。
“嗯……嗯……嗯……滋……滋……嗯……”
她放棄抵抗了,任由我的舌頭在她的口中翻攪,甚至不自主的吸吮我伸過去的舌頭。我狂烈的吻著她,一手搓著她的乳房,一手外撥弄她的小妹妹。我一直吻到她開始扭動起來,雙腿絞來絞去,使勁的夾著的手,仿佛不讓我的手深入,又似乎在催促我進去,而淫水一直不斷的流出來,濕了陰毛。她將恥骨前端,陰蒂頂在我的小腹下部,用力研磨,而且恥骨聯合處不斷小范圍高強度扭擺著,雖然幅度不大,但是獲得的快感卻非常強烈,小姨子已經放棄了抵抗開始在享受。
“啊~~~ 姐夫~~~ 啊~~~ 姐夫~~~ 啊~~~ ”小姨子放鬆身子把腿張開,示意我褪下那條狀物。
“不要再動了,不┅┅要┅”,她口裡拒絕著,但下體卻在我巨大的龜頭上磨裟著,我用龜頭在露出她的洞口攪動“,啊┅┅啊┅扣子┅┅在┅┅在左邊┅┅我受不了┅啊啊┅┅快進┅┅啊!”我突然拉著她猛力向下一扯,同時下體向上猛烈一頂。她啊的一聲慘叫,同時身子跳起來,但是因為我雄壯帶鉤的狼牙棒還從內部控製著她,所以剛剛彈起來的身子又重重地落回來。我隨之向上一頂,很巧妙很暢快地頂到她的花心正中。她又是啊的叫起來,身子也有了融化般柔軟下來的感覺,我感覺她的渾身都柔軟無骨般依附在我身上。
她的甬道是這麼的緊湊,以至於我都感受得到不同尋常的肌肉收縮壓迫。
看著她小心翼翼地上下調整身體,閉著雙眼滿臉迷醉的小模樣,我忽然猛力向上一頂。一頂就就完全貫穿頂到花心!一頂就擊潰了她的控製!
一頂就將她擊倒!
我從下往上,發起了連串的攻擊,令她再也說不出一句完整的話!
她乾脆牢牢抱扣住我的脖子,放鬆了下體,任由我狼牙棒對她肉蒲花園無情摧殘。她除了掛在我身上放聲淫叫喘息以外,再也不能做反抗了。她的蜜穴甬道緊湊狹小,受到一種恍若撕裂的快感,讓她軟化下來,猶如肉糜一般癱軟。淫叫聲低緩下來,取而代之的是嚶嚀的喘息聲,完全抗拒不了猶如潮水滾涌而來的快感。
她的身子在微微顫抖,很明顯我一番狂猛的衝刺促使她達到了高潮。她已然無力抗拒我的擺布,只能喘息著痴迷地注視著我,腰肢微微顫抖,顯然剛才高潮的余韻仍然存留。我的狼牙棒又一次擠開她窄小的蜜唇,深深地夯了進去。她渾身一震,腰肢向前面一挺,臀部向後一縮。
“啊!好刺激,你真的太強大了,我┅┅啊┅┅啊┅┅啊┅┅啊啊啊啊!”
我的連番重錘夯擊讓她再次難以自如說話,只能淫聲叫喚來抒發心中痕癢快感。我一邊衝刺,一雙手掌箕張,扣在她柔軟雙峰上。她搖晃起了腰肢,帶動我不由自主開始猛烈衝刺起來。非常強烈得吮吸和夾緊從她的甬道中傳過來,我雙手扶在她臀部上,連環撞擊,開始我的招牌動作:每秒抽插頻率高達4 -6 次的抽插。而且每次插入攻擊的角度都有細微的不同,或左或右或上或下或旋轉過抖動或攪拌。如此這般,她再次被我搞得瘋狂起來,雙手無力的揮舞,似乎己經完全失去了控製。
我故意抽出狼牙棒,只用巨大的龜頭在她的陰道口微微地有點插入的樣子,她不由自主的收縮著恥骨、臀部的肌肉,並發力向上翹起臀部希望我能真正插入。
“你┅┅你┅┅到底┅┅啊啊啊啊!”
“你在摺磨我呀!我受不了┅┅快點插┅插深點┅┅求你┅”“你┅┅你┅┅到底┅┅啊啊啊啊!”
她還沒有說完一句話,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,狠狠扎進了她洪水泛濫的肉蒲花園。潤滑的雨露令我抽插的動作伴隨著“撲哧撲哧撲哧”的聲音,給這單調的動作增添了異樣情趣。連環快速的攻擊讓她陷入狂亂狀態,搖晃著腦袋,發瘋地扭動起腰肢,前後左右地晃動著,希望能從各個角度給她帶來更爽的刺激。她力量很大,狂野的搖啊搖。而且甬道中傳來劇烈收縮,她的收縮很特別,先是在內部收縮一下,然後又在蜜穴唇瓣內側收縮一下。而我的抽插正好配上她的收縮,每次都被她箍在了龜頭冠狀溝附近,被夾緊的感覺快美難言。“哦┅哦┅┅來了,要死了,你!啊啊啊!要死了,死人!嗯┅┅要來了,要來了,┅┅”她浪叫著直起了身子,更加用力的收縮著內部。我的狼牙棒插入她整個緊湊的甬道,加倍地撐開,更深地貫穿。她無法忍受那種過于猛烈的撐開,搖晃著小小腦袋,長髮在腦後飛舞起來,一連串無法遏製的嬌吟從口中冒出。
“好大,好粗┅嗯┅┅嗯┅好硬、好熱┅┅嗯┅┅嗯┅好漲┅受不了┅┅嗯┅┅嗯┅┅嗯┅┅好強狀啊!”張開嘴慘叫,但是被我巨大狼牙棒的夯擊打得氣流不暢,聲音一下子嘶啞了。
“喔 ~~~喔~~~ 喔~~~ 喔~~~ ”小姨子不停扭動著屁股,“真舒服~~~ 喔喔~~~ 喔喔~~~ ”
小姨子高潮來了,淫穴緊緊的夾著雞巴。
“小姨子~~~ 我要~~~ 我要射了~~~ 喔~~~ 喔~~~ 喔~~~ ”
本想插多數下便拉出雞巴射精,但小豔輕輕用手抱著我的腰嬌吟的說。 “啊~~~ 姐夫~~~ 別離開…射裡面~~~ 喔~~~ 我要姐夫~~~ 射入裡面~~~ 喔~~~ 喔~~~”
我聽到小姨子這樣說,我更加興奮,加快插多數下,于咆哮著將滾燙岩漿噴射入她的淫穴。
良久,她才從巨大的快感中回過神來“我是不是太敏感了?”“我剛才完全酥掉了,你太強了,我從來沒有碰到這麼猛烈的攻擊,你的下體會轉彎,老是追著我的快感地帶打擊。”
“你的小穴真緊啊!”“你的身材真好!”兩手不規矩的分別在小姨子的乳房和陰戶摸來摸去“是嗎?姐夫喜歡嗎?”小姨子乾脆扯下了吊帶說“我的胸夠大嗎?
聽到小姨子這麼說,我就親了她的乳房一下。“你把我咪咪頭弄起來了…你真厲害,真雄偉啊,這個寶貝!好粗、好大呀!”說著用手輕輕撫摩著我的肉棒,肉棒在它可愛的又白又嫩的小手的刺激下,慢慢又硬了起來。
我將她的陰蒂扣在手指間,揉捏起來。小姨子又慢慢的呻吟起來“你又流了水!又想了吧?”我把濕漉漉手掌送到她眼前。“又流水了,真騷啊!”
她雙手握成拳敲打著我的胸膛:“你作死啊,啊?!…才沒有┅┅人家癢嘛!,我已經兩年沒做了嘛┅┅”
她用雙手捧住我的肉棒,然後用舌頭仔細地舔弄。用雙唇夾住我的龜頭,用舌尖頂在馬眼處鑽研。我感覺一種被倒灌的刺激從馬眼處傳來。嘩!想不到這靦腆羞澀的小妞居然還有這麼一招,隨著她香舌清顫,在我那細密的內部微微蠕動著,非常刺激,非常敏感。
“爽┅┅你的嘴巴真是太性感了┅┅啊┅┅爽┅┅舒服┅┅太舒服了┅┅真…舒服┅┅爽死┅┅了”
我半躺露出擎天一柱。我伸手過去“啊!不要┅┅”我把手伸到交合的地方掏了一把,滿手都是淫水。
她眼神閃爍著躲避,“人家兩年沒做了嘛!┅┅啊┅┅啊┅┅啊啊啊┅┅癢…人家又要了┅啊啊啊啊!”“劇烈的刺激讓她渾身都震顫起來。”啊!姐夫┅我要┅又要┅“說著又坐到我的大腿上。
“不要動,我來┅”她晃動屁股,找準地方,猛然往下一坐,就迫不及待地搖擺起來“啊┅啊┅啊┅真舒服!”她突然覺得有些放蕩,嬌羞無限地捂住臉,但是身子卻失去控製地扭擺起來,交合部位發出地糜爛聲音,身體內部潮水般涌流的快感,讓她難以矜持起來。她剋製著“恩恩”叫喚。
“喔~~~ 姐夫~~~ 你好厲害喔~~~~”
我感受到她體內一潮一潮涌流出來的淫液,隨著淫液猶如潮水般出來,她甬道內部也在猛烈收縮,猶如長蛇蜿蜒一般從內部不停的收縮到蜜穴開口,緊緊箍住我的肉棒。“放開點,小姨子!你想叫就叫吧,姐夫喜歡聽你叫喚”
她在我的胯上連續套弄了數百下。“嗯,嗯,我覺得好敏感好敏感,好酸軟酸軟,真的太刺激了,嗯,嗯,嗯,啊,啊,姐夫,你來┅┅日┅┅我┅┅好不好?”
她渾身震顫著,呻吟已經變成了嬌美的啜泣,翻下身來躺在床上,露出肉蒲花園,翹起蘭花指撫摸著自己的飽滿猶如饅頭的陰埠。如此迷人淫蕩的場面,怎能不讓我激動萬分。
我側躺下來,拉著她的小手去握我的小弟弟。她輕輕的叫了一聲,“啊……
啊……嗯……啊……癢……癢…“她舒服的忍不住發出呻吟,並開始套弄我的小弟弟。
“好姐夫,你快點上啊…!…恩…恩…啊……
癢……好癢……好……受不了……“她撒嬌地叫起床來。她的花蕊已充分展開,肌肉也已放鬆,淫水充滿了陰埠,可以展開激烈攻勢了!於是我扶好她我的臀部,開始用力抽插。再次失去理智的淫叫起來,她在模糊中喊到:”用力┅┅你┅┅要┅┅出來┅┅嗯┅┅嗯┅┅啊啊┅┅“。她的後面甬道似乎比起小桃的來還要緊湊,但是同樣被我無敵狼牙棒開墾得路路暢通。我將狼牙棒從她體內退出,但是稍微轉了一個角度,突然蛇深地插入她緊緊收縮的花芯,她發出意識模糊的叫聲,隨著有節奏向後頂……紅嫩的陰唇嫩肉隨著的抽干快速的翻進翻出,每次將陽具抽出時,就又有一大堆淫水流出。把兩人結合之處弄得到處黏糊糊的。
雪白的大乳房也隨著激烈的活塞運動不停的抖動。
“啊……啊啊……用力啊……插……插……快啊……啊啊啊……啊啊……用力……插死我……插!”“啊……好酸……好癢……又好麻……受不了……
插死我……插爛我的騷穴!“”喔!好爽啊!很久沒有這麼舒服過了。“”啊~~~ 入哂啦~~~ 入哂啦~~~ 姐夫~~~ 啊~~~ 你弄到人家~~~ 下面很癢喔~~~ 快點動~~~ 快干我~~~ 喔~~~ 喔~~~ 喔~~~ “小姨子不停扭動著屁股,不段說出這種淫蕩的挑逗話,使我覺得非常興奮,”喔~~~ 姐夫~~~ 喔~~~ 不要停~~~ 不要停~~~ 喔~~~ 頂到~~~ 頂到子宮了啊~~~ 喔~~~ 我要~~~ 我要泄了~~~ 喔喔~~~喔喔~~~ “我粗魯的抓住那對不停搖晃的碩大乳房,更激烈的頂上去……終于我無力了,整個人快要趴到床上,”姐夫…“她示意我翻過來,自己卻跨坐在我身上,拿起那根青筋怒張的大雞巴,緩緩的沉坐下去……,”好深呀……好漲、好爽……刺到子宮口了……天啊,還有半截沒進呢……。好硬、好粗……好舒服呀……“由於淫水過多,又有些空氣跑進陰戶,一時之間,隨著她雪白大屁股的起落,響起了噗唧噗唧的水聲,我越搖越起勁、越推越猛、越來越進入!激烈的抽插結果令她芳雪白的身體染成一片粉紅色,我們倆人的汗水混合在一起。她已經陶醉並沉溺在這淫海裡,完全沒注意到我的已經插入進了盡頭,並還在她陰道裡邊鑽動扭轉著。她瘋狂的猛搖晃著身軀,由其是她那蛇一般的細腰,更加的扭個不停,嘴裡大聲哀喊叫著:”姐夫,好舒服……好象插到底了呢……“
“天啊……好美呀……我要射了……”
“我也要泄了……”
“我們一起泄吧!”小姨子由於長期沒有做愛,猛烈的刺激竟然使她射起了陰精。
片刻之後,我們兩人抱在一起,我吻那對香噴噴又汗濕不已的大乳房,她用力頂住我不肉棒讓出來……
小姨子感到我的陰莖還硬硬的插在她的陰道中,她用手抱住我的脖子,用她俏麗的臉龐摩擦著我的臉讚歎的說:“你真厲害,等我歇息我還要…”
小姨子用手捏了捏我的陰莖的根部調皮地說道:“起來,英雄!起來…”我抱著小姨子兩條豐滿白皙的大腿,瘋狂的抽插著小姨子的小浪穴,房間裡又響起了“撲哧~~撲哧~~”的入穴聲。小姨子也淫蕩的向上迎接著我陰莖的插入,並媚眼如絲的盯著我。看著小姨子美麗淫蕩的容顏,我激動得快要爆炸,我把小姨子的雙腿壓在她的胸膛上,趴在小姨子身上,飛快的聳動著我的屁股,陰莖猶如飛梭般的插著小姨子的小穴,每次都頂在小姨子的花心上,小姨子真是個多水的女人,隨著我陰莖的抽插,淫水被陰莖象擠牛奶般的擠了出來,沿著小姨子的屁股溝流在沙發上,這樣大約抽查了一百多下,我的龜頭一陣陣發麻,不由得加快了插入的速度,小姨子知道我快要射精了,突然停止抖著她的臀部說:“我要讓你更爽!我要你從後面干我……這樣更深…”小姨子翻過來趴在床上。
“快干我,用力的…干我!!!干死我~~~ ,啊,~~~~,喔,干死我吧”我發狂的猛抽猛插。小姨子的陰唇隨著陰莖的進進出出,也翻進翻出的做著重複的變形運動。終于我的龜頭一陣跳動,大量得的精液急射而出,滾燙的濃精燙得小姨子“啊~~啊~~”亂叫,射精後的我無力的趴在小姨子豐滿的肉體上,大口大口的喘著起。小姨子愛憐的用手摸去我額頭上的汗水,然後座起身,我軟下來的陰莖隨著小姨子的淫水滑了出來。我低下頭,看著小姨子發紅的陰唇,她陰唇上占滿的淫水,在燈光下閃閃發光,小姨子的陰道口還沒有完全的關閉,能看見我乳白色的精液正從小姨子哪個紅色的小洞中流出來。小姨子抬手打了我屁股一下說:“還沒看夠嗎?色狼”。我又抱著小姨子親起來,小姨子的舌頭又軟又濕,親起來感覺好極